读《一句顶一万句》感受
更新日期:
读一句顶一万句
一句顶一万句是刘震云酝酿了三年的小说,整部书分为两部分,上部分写吴摩西失去了唯一能说的上话的养女走出延津;下部分写吴摩西养女的儿子牛爱国同样为了能找到能说得上话的人走到延津;这一走一回,延续百年几代人的命运生活轨迹。
小说彰显着刘震云富有特色的叙事风格,刘震云在北京大学演讲时说正如别人评价他的作品一样,第一次来到北京上大学的时候,北京火车站就把他“绕”了一绕;刘震云说他自己本身是个糊涂人,来北京第一天他便转向了,这一转就是三十年;刘震云说糊涂人在事情上再糊涂一把就能还原世界本来的面目,你让我往东,我偏往西,因为往西就是往东;你让我打鸡我偏要打狗,因为打狗就是打鸡。
前半部分描述了多个平凡人物的生活,叙事看似纷繁复杂繁琐,又一个人物跳到另一个人物再跳到另一个人物,但实际上所有的叙事都是按照一条主线展开,那就是人与人之间能不能说得上话,说的话交不交心,说的话能不能触及心灵。人们平凡生活的感情冷暖便只与人与人之间能不能说得上话有关。但是茫茫平凡苍生,每个人都在寻找能说的上话的朋友,每个人能够说得来的朋友却都是寥寥无几。这是中国国人心灵的百年孤独,这是每个国人都有的孤独体验。
书中的杨百顺因为再也不能在延津找到能说得上话的朋友而对延津伤了心,同样在百年之后,杨百顺养女的儿子牛爱国因为妻子跟别人跑了,与真正能靠的上的朋友闹掰了而对自己生活的地方彻底伤了心,这种相似的人生经历在书中每个平凡人物的身上都有体现,而同样这种孤独体验,便直入人心,能够产生巨大的能量。书中一个细节让我印象深刻,杨百顺养女的儿子牛爱国在走投无路的时候,第一个想到的是自己远在青海的战友杜海清,另一个临汾的同学李克智;不禁感叹,人活一辈子,到头来能指望上的只有两个。
牛爱国与自己的妻子之间没话,牛爱国后来却发现自己的妻子与婚纱摄影城的小蒋有说不完的话;牛爱国后来才知道自己的战友当时给自己出的主意让讨好妻子从根上起就错了。牛爱国在妻子跟别人跑了之后,满心的苦闷事事不顺心,便一次在喝完酒后满心积虑,便迫切能找一个人说,再不说就要憋死了,牛爱国第一个想到的是自己的战友杜青海,杜青海远在西北一千多公里以外,离得近的只有自己的朋友冯文修,以至于牛爱国半夜三更找到冯文修的家把自己三十五年来的苦闷一股脑说了出来。后来因为十斤肉钱的误会,牛爱国感慨多年朋友的情面竟不如十斤肉钱,这话传到冯文修的耳朵里便变了味儿,冯文修和牛爱国从此闹掰。与冯文修闹掰后,牛爱国再没有能说得上话的人,在一次运输中把车撞到山路的崖子上的树之后,便望着山下万家灯火,对自己生活的地方彻底伤了心,正如百年之前吴摩西寻找自己被拐卖的养女时苦苦找不到,吴摩西在火车站看到与老高私奔的吴香香,吴摩西望着偌大的火车站与人群感觉到再没有人情冷暖的时候,吴摩西彻底对这个地方伤了心,决意走出延津一样。
吴摩西在年轻的时候喜欢一个喊丧的叫罗长礼,喊丧是一个具有特殊意象的象征,正如现代人越是孤独越是要营造大的场景和氛围,在这一点上小说描述的其实是一种悲剧。
吴摩西的养女也就是后来被卖到陕西牛爱国的妈曹青娥年轻的时候不疼爱牛爱国偏心自己的哥哥,曹青娥几十岁以后却只与牛爱国讲五六十年前的事情却不与哥哥姐姐弟弟讲,在曹青娥快要去世的时候牛爱国才知道曹青娥与自己讲而不与自己哥哥姐姐弟弟讲是因为四个儿女中个个过的都不如意,而四个之中自己过得是最不如意的,曹青娥与自己讲五六十年前的故事与其说是一种讲话,更不如说是曹青娥借这些经历安慰自己;牛爱国在年轻的时候觉得妈不是妈,现在觉得妈是妈了。
曹青娥生前最能说得上话的是牛爱国七岁的女儿百慧,曹青娥给牛爱国说的都是五六十年前的事,跟百慧说的却是二三十年前的事,以至于曹青娥去世的时候让百慧读懂曹青娥的意思给他们听;曹青娥死后牛爱国仍然不知曹青娥去世时敲床头代表着什么,百慧说是曹青娥怕黑要带上床头的手电去找干爹吴摩西,牛爱国才恍然大悟,后来牛爱国才知道敲床头是因为床头里面有一封信,信上有吴摩西的孙子八年前跑到延津找曹青娥留的电话号码,曹青娥去世时敲床头就是想给吴摩西的孙子打电话问一句话。
为了找这句话,牛爱国辗转各地才来到延津,牛爱国这是想起来自己当初与妻子没话,却与在拉货时认识的章楚红却有说不完的话,章楚红当时提出要与牛爱国私奔,牛爱国犹豫不决最后闪了章楚红,章楚红曾经说有句话如果牛爱国跟他私奔了就告诉他,牛爱国现在不知道是什么,牛爱国想找章楚红却不知章楚红去了何处;同样是为了一句话,一句话顶一万句,百年之前,百年之后,牛爱国却需要这一句话解开自己的心结。
小说的主人公都曾想过要“杀人”,吴摩西年轻的时候因为父亲把唯一上学堂的机会留给了弟弟造就了弟弟后来表面上的光鲜和自己困难的处境而想过想要杀掉自己的父亲,给自己父亲出主意的拉大车的老马以及“衣着光鲜”的弟弟,在心里把他们杀了个遍,后来看到路边因不忍后妈折磨而在雪中睡觉的男孩才知道原来世上的事情都拐着个弯;同样在牛爱国与冯文修闹掰后冯文修公然传自己的坏话牛爱国想“杀”了冯文修。“杀人”在小说中是一个独特的意象,既是小说主人公发自内心的愤怒,又是一种内心的悲凉。
一句顶一万句是每个国人共有的孤独体验,这部小说是现实的,积极的,也是深刻的,沉重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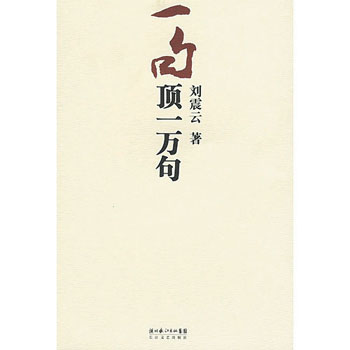
附上原书编者荐言:
一句胜过千年
安波舜
本书是刘震云酝酿创作了三年的小说。也是他迄今最成熟最大气的作品。
小说的叙事风格类似明清的野稗日记,语句洗练,情节简洁,叙事直接,有汪曾祺和孙犁等前辈作家遗风。因而本书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构成言说的艺术,都能拧出作家的汗水。更为重要的是,作家唯有用此语言,才有对应和表现作品的内涵:与神对话的西方文化和人类生态,因为神的无处不在而愉悦自在。人与人之间虽说来往不多,但并不孤独;与人对话的中国文化和浮生百姓,却因为极端注重现实和儒家传统,由于其社群、地位和利益的不同,由于其人心难测和诚信缺失,能够说贴心话、温暖灵魂的朋友并不多,反倒生活在千年的孤独当中。
这样的孤独体验每个国人都有;这样平视百姓、体恤灵魂、为苍生而歌的小说自五四以来却是第一部。
小说的前半部写的是过去:孤独无助的吴摩西失去唯一能够“说的上话”的养女,为了寻找,走出延津;小说的后半部写的是现在:吴摩西养女的儿子牛建国,同样为了摆脱孤独寻找“说的上话”的朋友,走向延津。一出一走,延宕百年。小说中所有的情节关系和人物结构,所有的社群组织和家庭和谐,乃至于性欲爱情,都和人与人能不能对上话,对的话能不能触及心灵、提供温暖、化解冲突、激发情欲有关。话,一旦成了人与人唯一沟通的东西,寻找和孤独便伴随一生。心灵的疲惫和生命的颓废,以及无边无际的茫然和累,便如影随形地产生了。
由此,我们忽然发现,中国人为什么活得这么累。
这种累,犹如漫漫长夜,磨砺着我们的神经祖祖辈辈。
为了摆脱这种孤独和累,书中的人们努力制造着声响和热闹。于是喊丧,便成了书中主人公杨百顺崇拜的职业。与戏子手谈,成了县长的私宠。但这无法改变本书人物的命运。就像今天,我们的民族还在继续为此付出巨大的成本和代价一样。不管你导演了多大的场面,也不管你举行了多少个庆典。因此,阅读本书是沉重和痛苦的,它使我们在《论语》和《圣经》之间徜徉,在与神对话还是与人对话的千年思考中徘徊……
当然,阅读本书也让我们感受到生命的执着和顽强。为了在精神上有所依托和慰籍,人们义无反顾地追逐“一句顶一万句”的身影,很像祖辈弯曲的脊背和那一大片脊背组成的苍穹。

附上一篇来自网络的书评:
来源:(http://book.douban.com/review/1972055/)
刘震云53岁了,在公共场合里总是穿着一件对襟的黑色夹袄,说是妈妈亲手做的,这让他看起来很像个乡下来的手艺人。刘震云写小说已经写了30多年,故乡延津的老乡们不觉得当作家是个多荣耀的事儿,就是个靠编瞎话为生的说书人。所以他也不觉得写作是件多么高尚的事情,他最讨厌的就是所谓的知识分子那种俯瞰苍生的态度,他觉得与其跟这些人在一起凑个饭局,说些言不由衷的大话,到不如跟村里的舅舅,表哥们聊天更有意思,更有收益。他经常回自己的老家老庄村。老家的父老乡亲,那些卖豆腐、剃头、杀猪、贩驴的,他能跟他们说到一起。他们说的话更接近生活的本质,更知心,“一句顶一万句”。
刘震云的外祖母生前给刘震云讲了一个故事,“她有一个叔叔,一辈子没娶上老婆,跟家里的一头牛成了好朋友。有一天这头牛死了,叔叔三天没有说话。第四天凌晨,他离家出走了。后来,四乡八镇都找了,所有的井也打捞了,不见叔叔的身影。”这个故事让刘震云很震惊,是什么原因让一个这样的一个普通的养牛人离开自己的故乡和亲人,要去到领一个陌生的地方?因为一头牛的死掉,自己熟悉的地方已经变得陌生,所以只能去一个更陌生的地方去寻找一种新的生活。在刘震云看来,这就是精神上的“高级”流浪和漂泊。不要说精神的痛苦只有知识分子才有。
怀着这样的一个想法,刘震云用了三年时间,写下了新的长篇小说《一句顶一万句》,书中的话是两个主人公,这两个主人公,一个叫杨百顺,一个叫牛爱国,他们在心里杀过人的“杀人犯”,一个人特别想找到另一个人。找他的目的非常简单,就是想告诉他一句知心的话。
“一个人的孤独不是孤独,一个人找另一个人,一句话找另一句话,才是真正的孤独。”小说中塑造了很多世间的百姓,卖豆腐的,剃头的,杀猪的,贩驴的,染布的,开饭铺的,还有提刀上路杀人的……每个人都在寻找一个可以说上知心话的朋友,一个人找另外一个知心朋友不容易,你可能跟这个人是好朋友,但是你们在一块的话未必能说得上话,其实比人找人不容易的是话找话,《一句顶一万句》反映了一种中国式的孤独和友情观。
“《论语》的第一句话就是: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一句顶一万句》的孤独就是对这句话的注解。”文学评论家李敬泽说,“不同于西方文学作品中人与世界的对抗产生的孤独不同,杨百顺他们的孤独又是另外一种孤独,杨百顺的问题是他总觉得这个世界上应该有那么一句话,应该有那么一个道理,他说不出来,他等着到茫茫人海中去找希望有个人能够说出来,能够找到,但是他找不到。他的孤独是他手里没攥着那么一个他自己绝对信的那么一句话。他想找那么一句话,这种不确定性,构成了一种更大的孤独。”
什么才是朋友?《一句顶一万句》里朋友的关系充满了不确定性,因为一句话,一件小事,知心的人可以瞬间一刀两断,就像刘震云说说:“朋友的关系是危险的。”生活的细节决定了生活的偶然,在刘震云看来,正是细节中的人和事,才构成了小说中所有命运的跌宕转折,因为中国人永远都是活在细节里的,而细节会变的,细节变了,生活变了,朋友也就变了,于是小说中的人物,不得不接受这种命运的变化,去另外一个更陌生的地方寻找新的生活。
“寻找”是《一句顶一万句》的母体,写作对于刘震云来讲也是一个寻找知心朋友的过程。他说不是自己创作了这些人物,是这些人物跟他出来谈话。他在《一地鸡毛》中找到了小林,在《手机》中找到了严守一,在《我叫刘跃进》中找到了刘跃进,这次在《一句顶一万句》中找到了杨百顺和牛爱国,还有传教的老詹,杀猪的老曾,剃头的老裴……。就是这些小人物,却都是刘震云真正可以说知心话的朋友。“与书中人物结伴而行,晓行夜宿,披肝沥胆,说的都是知心话”,他找的人越来越深,与这些人谈的话题也越来越深,《一句顶一万句》谈到了杀人,绿帽子,和孤独的事,这些话是凶险的,只能跟知心的人说,与杨百顺和牛爱国说这些话,刘震云也会被自己突然写出来的句子吓一跳,“知心话绝对不是滔滔不绝的,所以书里的句子很短,句号很多,没有形容词,朋友在一起谈知心话的时候那些兄容和比喻是没用的。朋友在一起说的都是朴素的话,真实的话,和知心的话,这三种话是有力量的,所以我觉得我自己写的比原来好。”
有了这样的写作,刘振云就不再孤独。他说摆脱孤独是他写作的动机原因和目的,在书里交了朋友就也不孤单。在他不写做的时候反倒累了,总是感觉没着没落,“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我是谁了”,“写作的每一天都很愉快,不写作的间隙却很沮丧,就像喝酒一样,有酒喝喝醉的时候很愉快,第二天醒了就很难过”,所以刘震云说自己的最佳状态,就是像李白一样“但愿长醉不愿醒”,但他是要醉在写作里的。
“我肯定是个好作者,因为我写作不累”。刘振云说,“写作这个不是祖传的,我外祖父的爹曾经开创过一个村庄,叫老庄村。他逃荒逃到一片盐碱地,就靠熬盐、熬碱为生。我觉得他是个智慧的人,一个新创的村庄叫老庄,显得深,因为新,确实也有点虚张声势和作贼心虚的感觉,出门就吆喝,老庄的盐来了,老庄的碱来了,人家说老哥,怎么没听说过这个村啊?他说“有点远!”远来的和尚会念经,于是老庄的盐碱也就形成了品牌,周围村庄吃的都是老刘家的碱和盐。”
“我外祖父的爹真是个聪明人,这聪明背后,是河南人面对生活的态度。经常有人说我是幽默的,这个幽默不是话语的幽默,真正上升到文学的层面,话语的幽默会让人讨厌的,我的幽默是事情本身的幽默,也不是事情本身幽默,是事后边的这里理很拧把,明明看着不行的事情,大家都要去做,不做到成了不对的,这就变成了幽默。我们面对艰辛和苦难的时候,幽默会把铁像冰一样融化掉,如果说祖传,我的幽默的出产地也是我外祖父的爹开创的那个老庄村的盐碱地里,这个地点是祖传的。在苦难的地方长出幽默的大树,会更幽默。”刘震云说。

